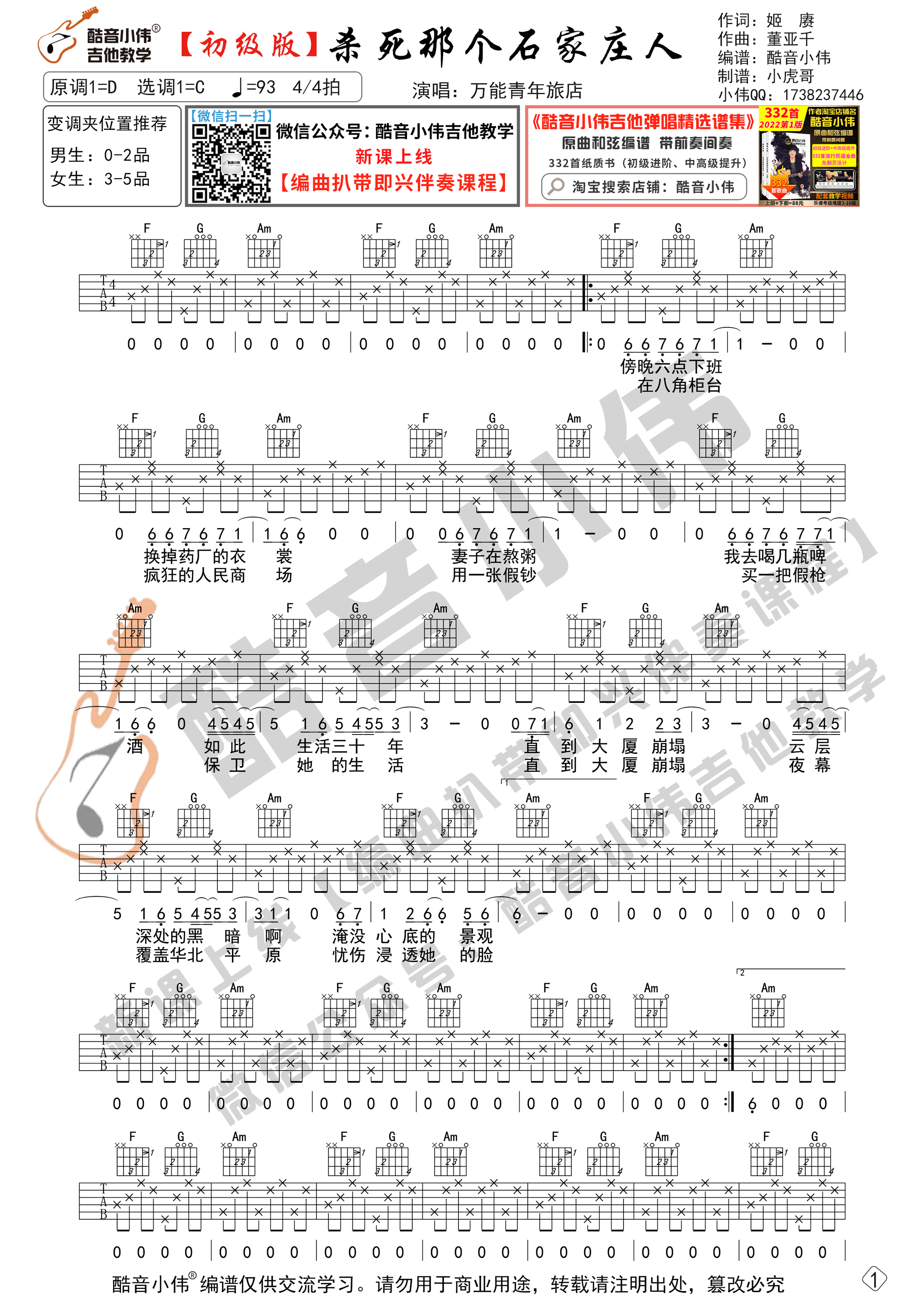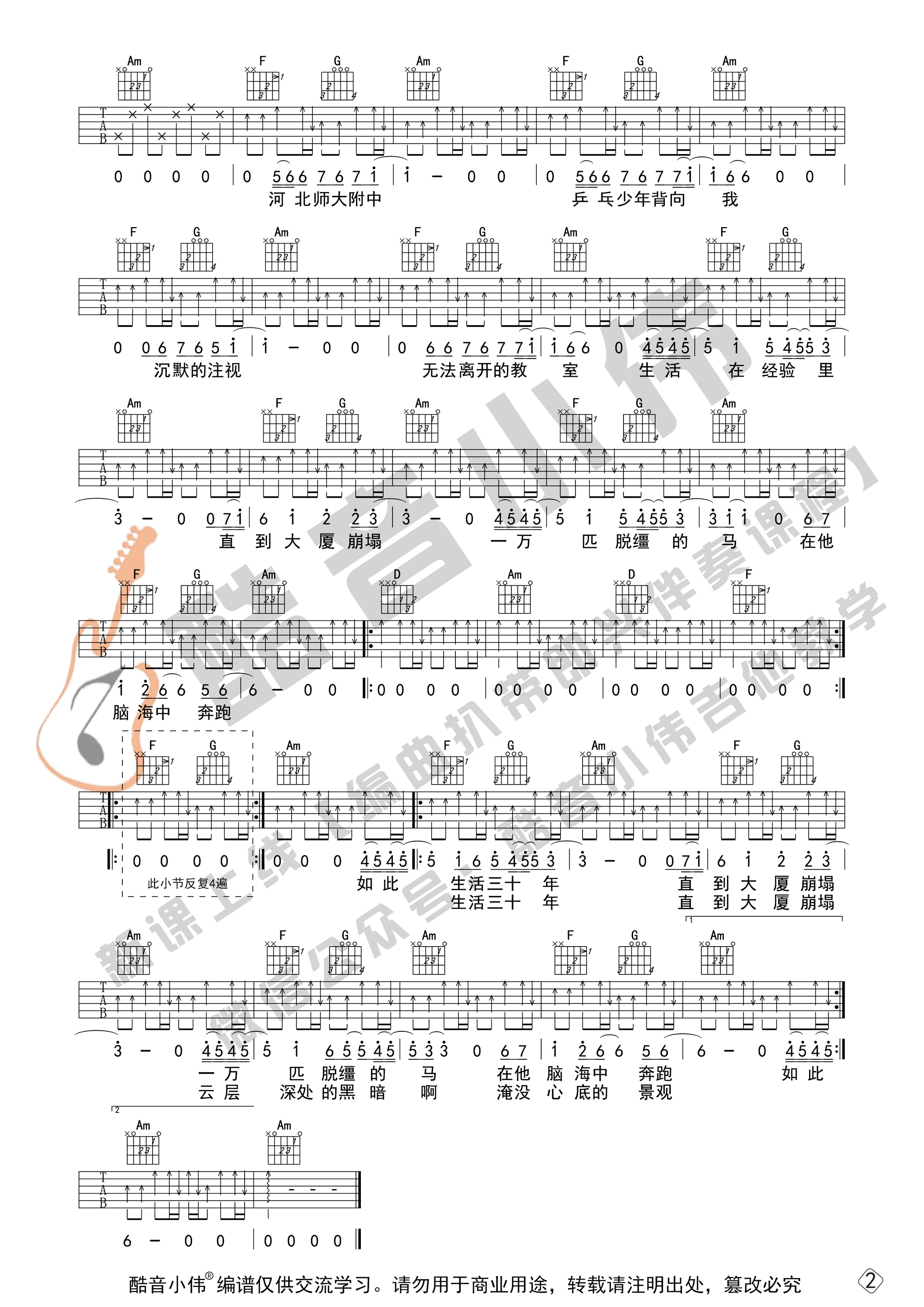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以冷峻的笔触勾勒出工业城市变迁中的个体困境,在钢筋水泥的背景下展开一幅精神困顿的生存图景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药厂、家庭、电视机等意象构成封闭的生活闭环,暗示着工业化浪潮下人类活动被异化为机械循环。乒乓少年与云层深处的黑暗形成强烈对比,既是对理想主义消逝的隐喻,也揭示物质繁荣表象下的精神空洞。副歌部分用“如此生活三十年”的重复吟唱,直指时间在僵化体制中的凝固状态,而“大厦崩塌”的意象则宣告传统价值体系的溃败。歌词将个体命运嵌入时代转型的裂缝中,那些被掏空的愤怒与无处安放的惶惑,最终化作一句充满荒诞感的暴力宣言。全篇通过克制而精确的细节白描,呈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,普通工人从集体主义信仰跌入价值真空后的存在性焦虑。石家庄在此既是具体城市又是精神符号,记录着被时代列车甩出轨道的人群,如何在记忆废墟里徒劳地寻找身份认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