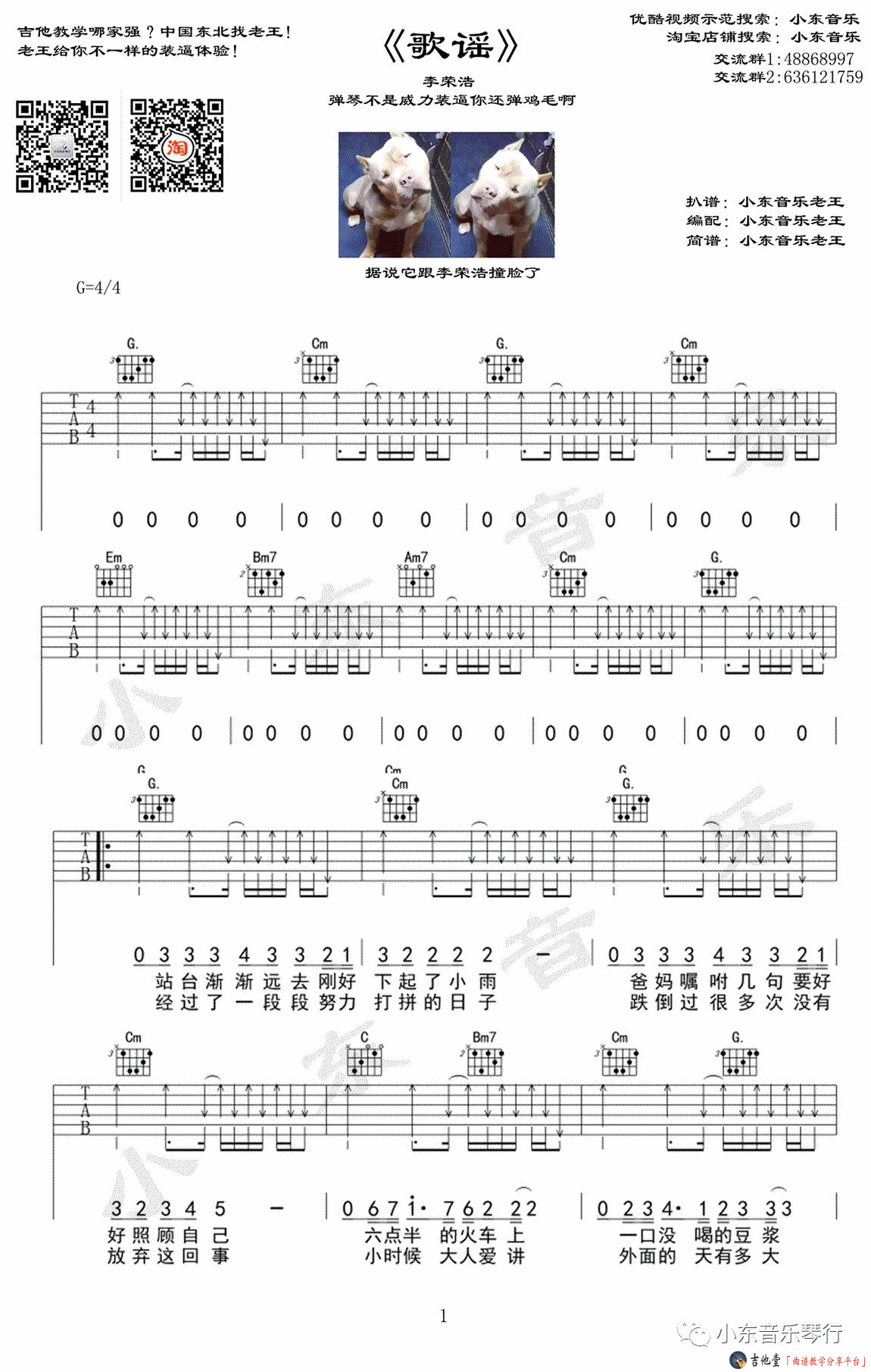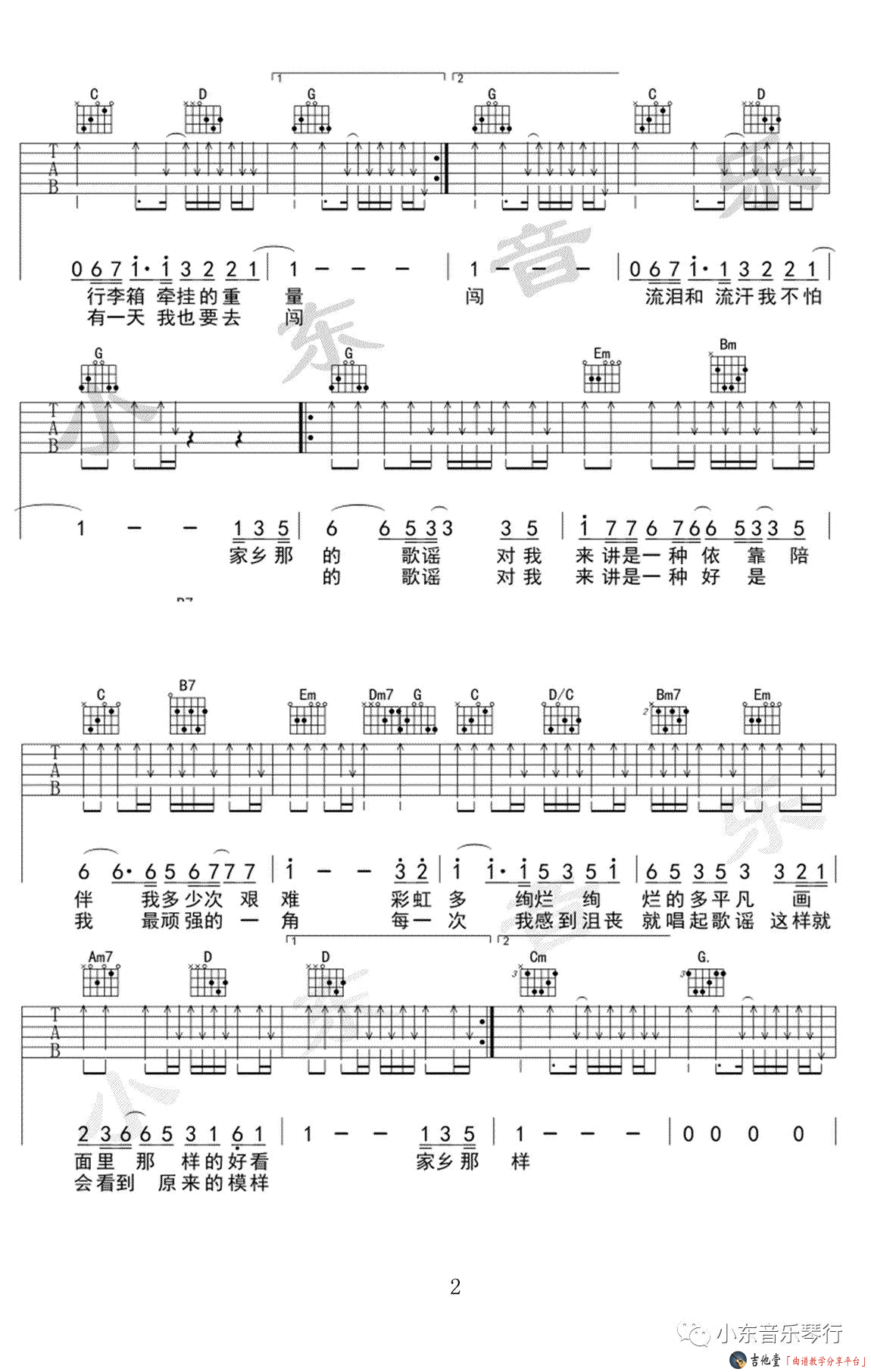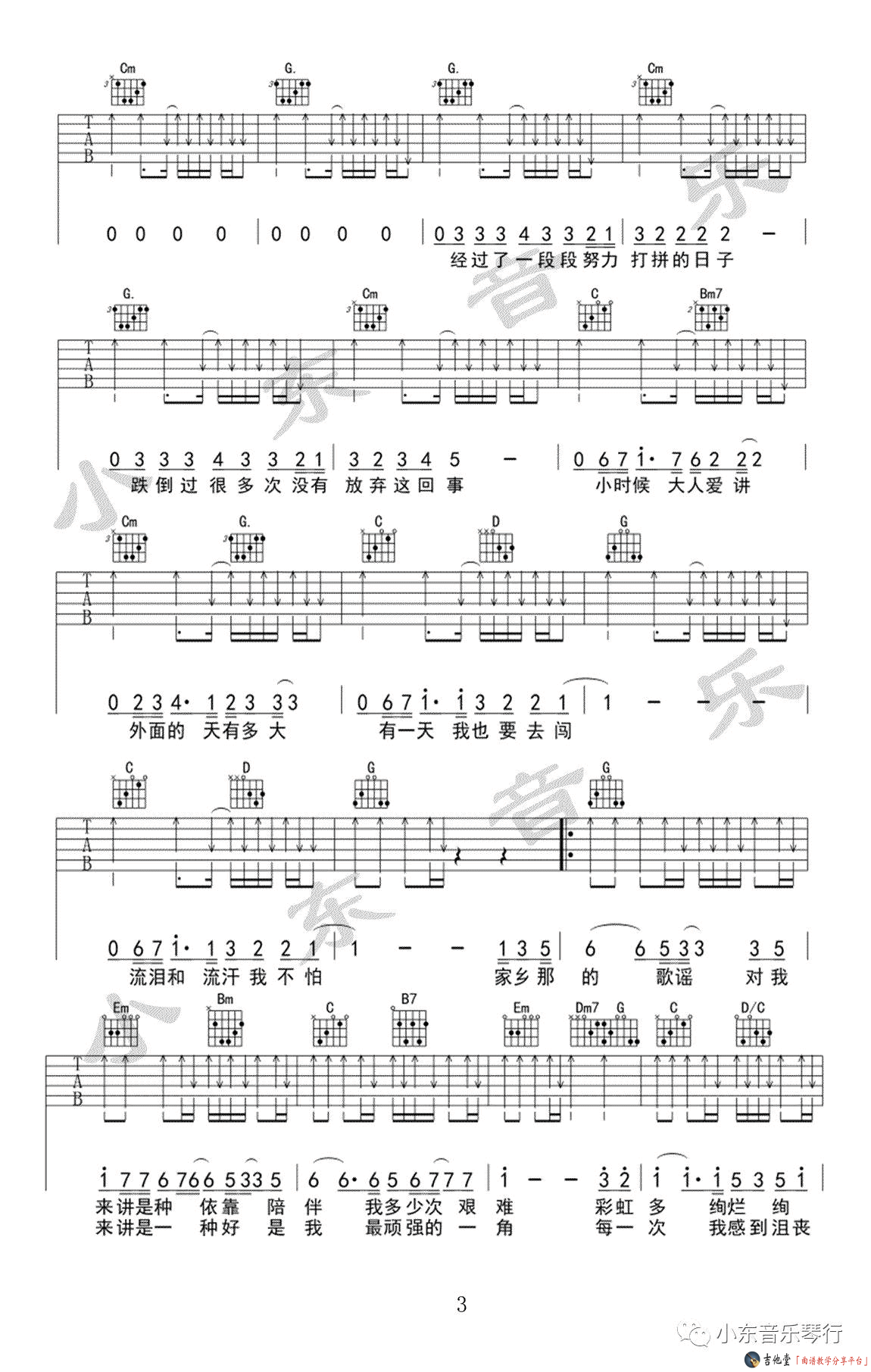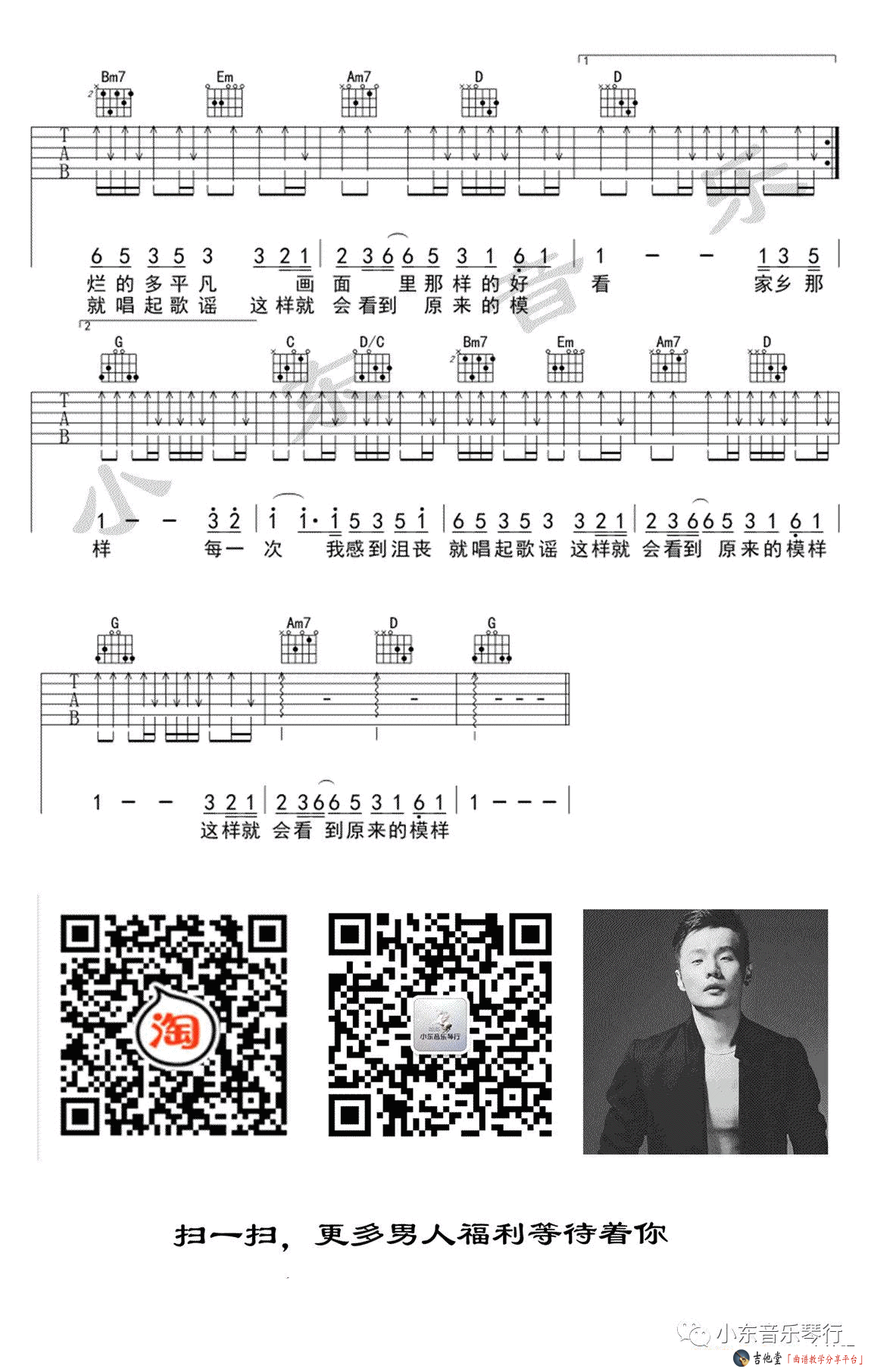《歌谣》以质朴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民间烟火气的精神家园,通过柴火灶、老槐树、青石板等意象群落的铺陈,将乡愁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生命记忆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哼着那首未完成的调"构成核心隐喻,既指代个体生命经验的残缺性,又暗示民间文化传承的永恒流动。炊烟与星空的垂直对应构建了天地人神的四维空间,而"磨盘转着年岁"的拟人化处理则赋予时间以循环往复的农耕文明特质。在表现手法上采用通感修辞,将"晒谷场上的阳光"转化为听觉化的温暖记忆,使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产生和弦共振。那些散落的童谣片段不仅是声音化石,更承载着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基因,屋檐下摇晃的辣椒串构成红色符码,与后半段出现的"新酿的米酒"形成味觉闭环。作品最终超越具体地域限制,通过"所有漂泊都长着相同的根"的哲学表述,揭示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原乡情结,在碎片化时代为听众提供了一种文化认同的黏合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