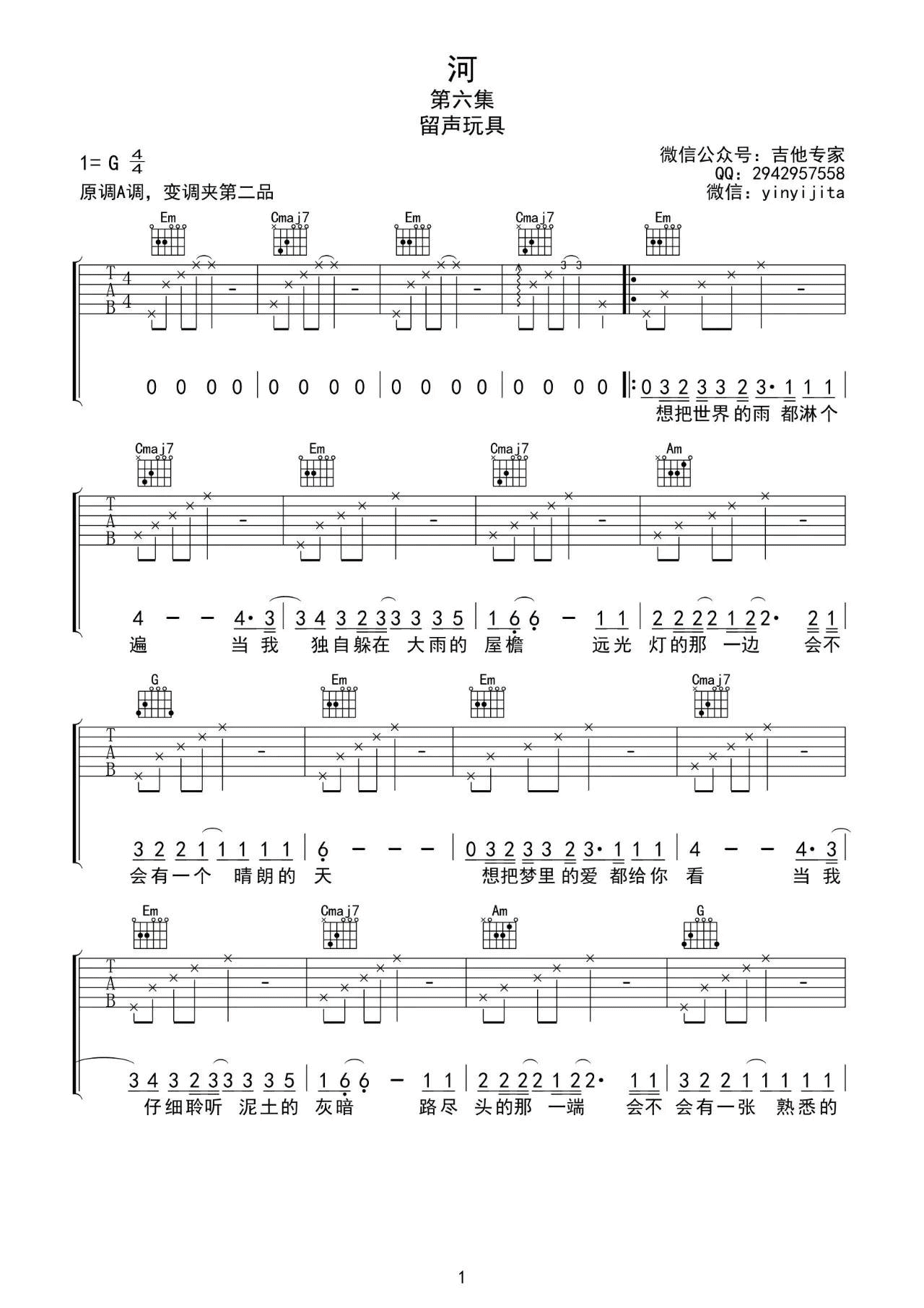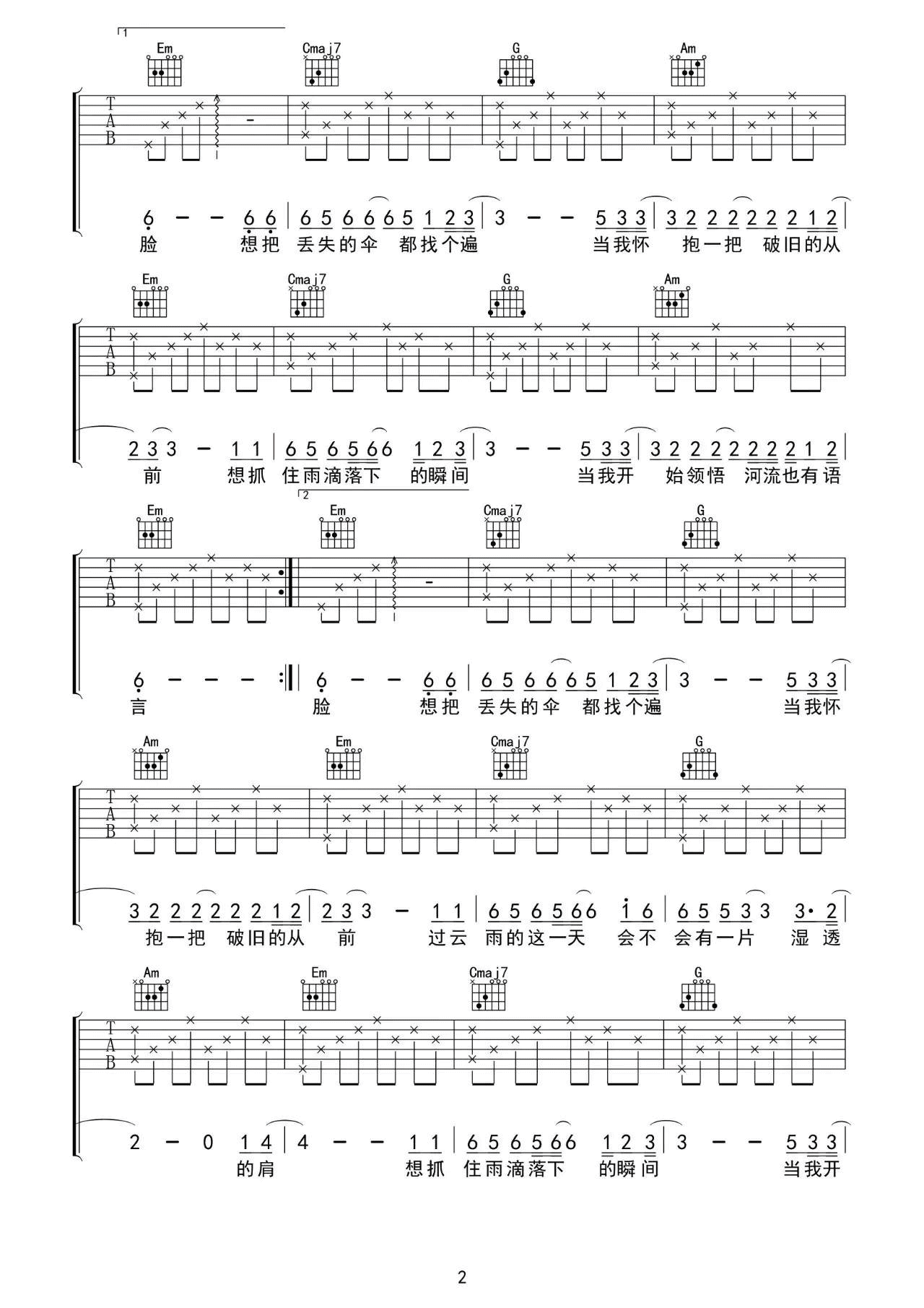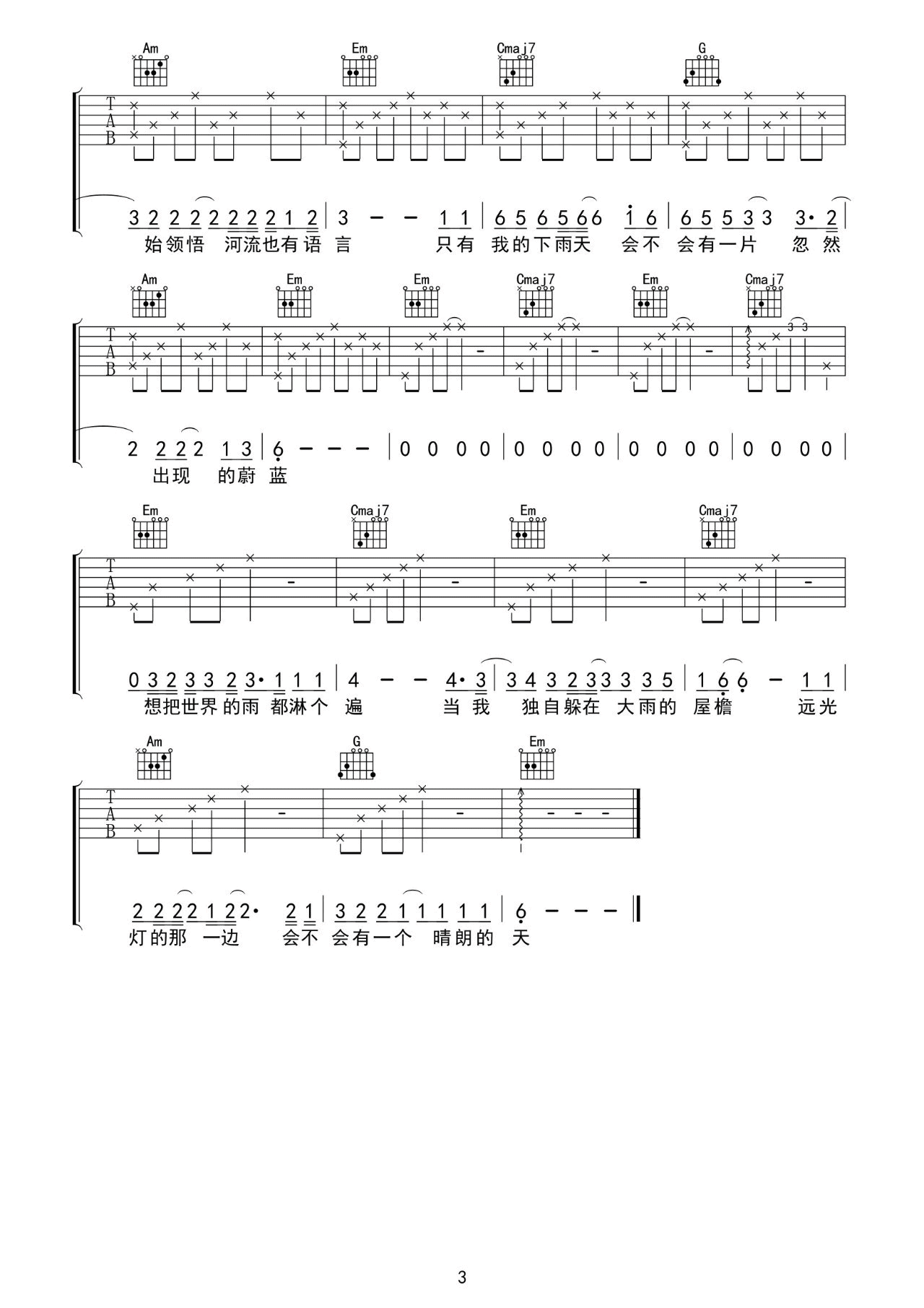《河》以水的流动形态隐喻生命的本质状态,通过具象的自然意象展开哲学思辨。歌词中蜿蜒的河道既是地理实体又是命运轨迹的象征,暗合老子"上善若水"的东方智慧,水流遇石则绕的柔韧与水滴石穿的刚毅构成辩证统一。浑浊与清澈的交替出现揭示存在本身的复杂性,泥沙沉淀的过程暗示时间对真相的过滤作用。反复出现的"奔向"动作形成贯穿全篇的生命驱动力,与河流最终消逝于海的宿命形成张力,既呈现西西弗斯式的永恒抗争,又暗藏庄子"物化"思想的超脱。河床作为记忆载体出现时,其上的刻痕与倒影构成虚实相生的镜像关系,水面同时作为分离与连接两个世界的介质存在。雨季泛滥与旱季枯竭的极端状态,隐喻着情感与创造力的周期性律动。歌词最终将河流的归宿升华为气态循环,突破线性时间观,在水的三相变化中完成对永恒议题的诗意诠释,使具象的自然现象获得形而上的哲学重量。